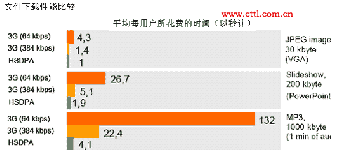宽带提速降费备受社会关注。运营商方案被指没诚意,那么如何做才算是真有诚意呢?宽带网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能否支撑资费断崖式下降?要实现偏远地区百姓的宽带可获得,互联网企业是否也应该分摊普遍服务成本?我国的电信市场到底是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如何实现互利共赢?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近日接受了《人民邮电》报记者的专访,详解宽带提速降费背后的经济逻辑。
通信网络建设及维护需要巨额资金,成本回收期至少七八年,4G上马后,部分运营商3G网络资产将逐步被弃置,成本回收无望,资金压力大,运营商需要逐步消化。互联网企业租赁网络资源有成本,但同国际水平相比较低。
对于互联网企业租用电信公司网络资源的成本问题,史炜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哪天他们自建网络了,就说明网费高了”。根据年报数据,2014年腾讯公司网络成本(租用运营商带宽及服务器托管费)占总成本的7.7%、占经营收入的5.4%,百度公司这两项指标分别为7.9%和5.8%,乐视公司分别为4.2%和3.6%;而同期运营商网络投资占收比达34.6%,网络成本占总成本比更高达65%(以中国电信为例)。而在国外,互联网公司、OTT公司所支付的带宽服务成本占整个成本的比例普遍高于我国。
另外,互联网公司的核心价值和电信运营商有着显著的不同。互联网公司是轻资产,它们关注的核心是在网上可以形成多少增值服务,但是运营商的核心则是普遍服务,首先要保证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其次才会考虑增值服务。尤其是在技术更新换代快的移动领域,运营商建设网络的花费之高超乎外界想象。随着标准的提高,从2G到3G再到4G以及未来的5G,每一次网络升级运营商几乎都需要投资。
我国是在2009年1月发放的3G牌照,2013年12月发放的4G牌照,近5年时间每家运营商3G投资成本约为2000亿元。而中国移动去年一年的资本开支就超过了2000亿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预计4G建网总成本均将达到2000多亿元。从国际经验来看,通常3G网、4G网投资回报需要7~8年。以中国电信为例,投巨资建成的3G网络才使用了6年即要开始投资建设4G网,可以说3G连建网成本都没收回来,但在2019年前,3G网络投资每年依然会给中国电信产生高达200亿元的折旧成本。尽管如此,运营商依然努力让消费者享受高速网络的红利。2014年6月,中国电信推出的4G网络速度相比3G增长超过10倍,但资费便宜了30%,今年5月,为响应“提速降费”号召,又降了30%。但消费者还是乐于用韩国等4G发达市场的资费跟我国相比。史炜认为这并不科学。以韩国为例,它国土面积小,人口密集,运营商建网难度比我国运营商小很多。另外,韩国4G发展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开始接近4G回报期,其降价空间明显要比我国刚上马4G要大,为此消费者应该再多点理性和耐心,给我国运营商建网、发展用户、进一步降价更多时间。
我国地形复杂,运营商承担繁重的普遍服务义务,迄今所铺设的网络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进程中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OTT企业是否该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值得探讨。
史炜告诉记者,最近,他在西部云、贵、川等边远地区调研时深切感受到,即使偏远贫穷的地方,信号覆盖也很好。这就是中国运营商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令人佩服。互联网公司则没有。普通消费者可能更在乎的是能不能打电话、玩微信,但若要保证农村地区的用户能享受到跟城市用户一样的服务体验,靠的就是运营商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
中国地形结构复杂,三分之二是山区,其中还有约一半的面积是无人区。在这些地区,建设和维护通信网络难度之大、成本之高外人很难想象。史炜称,按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的普遍服务在世界上是解决得最好的国家。我国“村通工程”迄今成绩显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5月发布的文件,到2015年年底,95%以上的行政村通固定或移动宽带,实现乡镇以上地区网络深度覆盖,4G用户超过3亿户。到2017年年底,8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到村,农村宽带家庭普及率大幅提升;4G网络全面覆盖城市和农村,移动宽带人口普及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史炜认为,我国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三大运营商在“村通工程”中所做的努力将对农村地区未来的经济建设发展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
史炜强调,普遍服务是否开展顺利的根源在于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机制。我国现在针对普遍服务设有一定的资金补偿,但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有效的机制对于解决普遍服务问题有重大影响,比如政府采购机制。以美国为例,在执行普遍服务项目时,均实行的是政府采购、运营商建设、政府买单的模式。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要强调政府采购,建立相关机制,值得期待。史炜认为,我国的普遍服务机制,什么时候真正落实到政府需求、企业建设、政府采购,什么时候就会行之有效。
国外目前针对互联网企业是否应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已有讨论,法国电信管制机构ARCEP此前就曾要求Skype按当地法律以电信运营商的身份进行注册,并同时承担开通急救电话服务、在合法条件下允许司法监听电话等运营商应承担的责任。我国目前也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提供类似电话功能的应用,史炜认为,在这类互联网企业是否应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问题上,我国也可以适时展开调研。
通信业是服务业,而非工业,以工业经济时代评判标准来理解垄断并不合理,中国基础电信领域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不断有新进入者,并不存在公众理解的那种垄断。
媒体和网友往往把通信业资费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垄断。史炜告诉记者,有关通信业垄断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我国3G牌照发放之前就有争论。通常有两种观点,通信圈认为不垄断,经济学家圈认为垄断。经济学家是按工业经济评价的。从工业经济特征来看,垄断一般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自然垄断,国外电信业几乎都经历过这一阶段。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电信运营商最初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网络是国家建立的,提供最基本的语音服务,这样诞生的企业必然是垄断的,石油、金融等行业均是从自然垄断开始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垄断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会进入市场化垄断阶段,这时政府管制机构会直接根据市场份额对企业进行约束,比如美国当年分拆AT&T公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韩国也对曾经一家独大的SK电讯有约束条款,只要其市场份额超过50%就处罚。通过政府干预加剧市场竞争后,市场格局仍可能是垄断的,但这种垄断的存在是合理的,是由行业特点造成的。比如印度的运营商非常多,但行业格局依然是垄断的。
史炜指出,我国情况与发达国家有明显不同。我国是从计划经济演进而来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行政化的垄断,当年的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电信分成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都是行政性决策。因此,我国通信市场是由自然垄断到行政垄断,又混合到中国特有的行政加市场的垄断。此外,三大运营商均是央企,国有资本占据绝对资本结构,这是判定三大运营商是否形成垄断的根基,很多经济学家指责电信运营商垄断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通信业和工业经济并不一样。三大运营商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而服务业和工业的垄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些经济学家在判定通信业垄断时直接套用工业经济模型,认为企业规模大,比如市场份额超过50%,便会带来衍生的定价权、资源优先占有权,进而形成垄断,史炜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解释,我国通信业并不存在现阶段服务经济框架下的垄断。加之近年来通信业持续价格大战,企业运营压力巨大,相较电力、石油行业的竞争激烈很多,为此从市场现状看运营商并未形成垄断。但他同时指出,由于我国通信业长久以来没有新的进入者,为此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垄断,是一种正常业态,一旦有新进入者,客观垄断即破除。
要正视互联网企业和电信企业的天然差异,促进互利共赢。运营商要对接的是企业,要做好智能管道工作,而OTT公司对接的则是消费者。
史炜指出,构建互联网企业与电信运营商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对于促进信息消费和推进“互联网+”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互联网产业的分层结构来看,电信企业处于基础网络设施层,建设和运营底层宽带与移动网络,互联网企业居于内容和应用层,“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共同构建当前的生态网络,形成巨大的网络外部性,推动了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电商企业发展迅猛,发展水平超过美国,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水平。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智能终端的崛起,云管端技术不断成熟与发展,业务和网络分离加快,互联网企业逐步占据产业链核心,经营业绩如日中天,而电信企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率直线下滑。互联网企业的飞速发展繁荣了内容和应用市场,为电信企业增加一定的流量收入,但同时互联网企业还推出众多具备通信功能的业务,通过免费等方式直接替代电信企业的核心业务,电信企业流量收入的增加远远无法弥补其业务收入的损失,替代效应逐步占据主流。可以说,运营商在为互联网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的同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反而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两类企业的这种偏利共生关系如不能有效改善,长期必将降低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投资能力及意愿,从而破坏整个信息通信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互联网+”战略的顺利实施。今后几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需要互联网企业承担起应有的义务,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网络设施建设、使用等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更要高度重视自己的管道。管道概念跟原来完全不一样,有些是民营资本做不了的,运营商一定要做智能管道。智能管道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我们到底往上装什么样的内容,哪些内容通过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金融、产业的方式开放,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
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的“互联网+”在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层面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对于运营商来说,“互联网+”是运营商和企业之间的对接,而OTT公司的“互联网+”则是互联网和普通消费者的对接,史炜如此解读。
责任编辑:饶军